滩涂“挖宝”、“围网”捕鱼:赶海生意经
生活在滩涂上的沙虫、蛏子和车螺(丽文蛤),追随着潮汐的节奏,退潮时,蛰伏在泥沙之下,涨潮时,再将身体探出沙面觅食。作为游客,你只需带上一把小铲子、一小瓶盐以及一个塑料小桶,就能在潮水退去的海滩上“挖宝”。
作为时下最流行的旅游项目之一,赶海完美切中了人们的探索欲等情绪。大海就像一个巨大的盲盒,你永远不知道,下一块石头底下、下一个洞穴里藏着什么。
在广西北海夏日的旅游旺季,滩涂上几乎每天都有数万名游客,把滨海公路堵得水泄不通。自十年前赶海旅游兴起后,赶海已不单单是原住民的谋生手段或游客的自发娱乐,而逐步演化成一门炙手可热的生意。靠社会化媒体的“引流”走红后,更有数倍的新玩家涌入,为赶海者提供向导、接送等各类服务。
但在“价格战”之下,良莠不齐的服务的品质也消耗着行业口碑:比如“挖宝”时找不到向导,商户提供的服务“货不对板”,以及在滩涂上载客的摩托车通过改装,严重超载,存在安全风险隐患等。
而在社会化媒体上,北海只是赶海的热门旅行目的地之一,从辽宁到海南,赶海项目几乎火遍了整条海岸线。在赶海生意热潮中,商户赚到了钱,游客获得了体验,承担代价的却可能是生态环境。
数以万计的游客,每天在滩涂上扫荡式地“挖宝”,是否会给沿海滩涂的生态带来影响?广西科学院副研究员王俊杰告诉南方周末记者,不科学的赶海行为可能破坏海草床、红树林,还可能伤害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鲎,而潮间带生物量的减少,也可能给候鸟觅食增加了难度。
赶海只需要简单工具,门槛不高,但不同游客的收获差距悬殊,重点是有没有一个“好师傅”——有经验的向导能一眼看穿滩涂之下的秘密。
“两个孔、‘8’字形的是蛏子洞,在洞口撒上一点盐,蛏子马上就钻出来了。”资深向导吴老二告诉南方周末记者,骤升的盐度会被蛏子误识别为涨潮信号,触发其返回水面的本能反应。而扁扁的、稍微凹下去一点的洞里面藏着车螺,它不像蛏子一样埋得那么深,只有约5厘米,用耙子轻轻一耙就能挖到。
本地渔民在挖沙虫,这是当地人主要的生计来源之一。南方周末记者 林方舟/摄
吴老二的家在北海赶海网红地——银滩镇下村,距离滩涂只有几百米。六七岁起,他就开始在滩涂上挖沙虫,为自己挣学费。时至今日,挖沙虫依然是当地村民重要的生计来源。
由于产量有限,沙虫价格一直很坚挺。每天挖沙虫的窗口期是在退潮后的5小时左右,吴老二靠挖沙虫每天能赚取三百多元的收入。
相较挖车螺、蛏子,挖沙虫更有挑战性,技巧和体力缺一不可。先找准洞穴——针孔大的小洞周围有沙粒微微鼓起,工具选择锄头或铲子,运用爆发力,以最快速度挖掘,抢在受惊的沙虫逃跑前将其捉住,整一个完整的过程在几秒钟内完成。
“做导游还是轻松一些。”赶海旅游旺季期间,吴老二会专门做向导。2025年暑假,雇佣吴老二的赶海商家一天最多能接待近千名游客,每天至少要聘请6个向导。资深向导的工资是300元/天,普通向导和大学生兼职向导分别是200元/天和100元/天。
2015年,本地青年“沙虫哥”在湛江的养虾生意失败后返乡。脑子活泛的他,率先尝试收费带领游客赶海,北海第一家赶海商户自此诞生。
据“沙虫哥”回忆,十年前,滩涂上基本上没有游客赶海,只有渔民在挖沙虫。这项被创造出来的需求踩中了人们的喜好,“沙虫哥”每天接待的游客数量,渐渐从几个人上升到几百人。
同乡人开始纷纷效仿,到2019年,当地已成立十几家赶海商户。旺季时,“沙虫哥”每天接待700人左右,甚至还把客源介绍给其他同行。“沙虫哥”雇佣了20个员工,盖起一座五层小楼,还干起了民宿生意。
赶海商户“红树林天天赶海”的生意在2024年达到了最高峰。老板张智英说,当年共接待了约4万人次,营业额达到110万元左右,是当年北海的赶海行业老大。
据环保组织“广西生物多样性研究和保护协会(美境自然)”统计,自2015年至2024年,下村经营赶海生意的商户只有十几家,而2025年,猛增至66家之多,其中许多都是到此捞金的外村人。
一些商家开启了价格战。2025年之前,本地商户统一将赶海旅游定价为38元/成人,而现在许多商户降价至19.9元/成人,叠加网络站点平台发放的优惠券,甚至能达到9.9元/成人。
这意味着商家想要盈利,就要让每位向导多带游客。旺季时,有的向导甚至同时接待一两百人。这也让赶海的想象和实际体验相差悬殊:短视频中,随便一挖都是“狠货”;现实中,顶着烈日和高温,穿过熙熙攘攘的人潮,通常只有盲人摸象般的搜寻、枯燥的重复和鸡肋的收获。
游客赶海的滩涂入口,与广西北海滨海国家湿地公园标示的红树林保护区域“一网之隔”,部分拦网已被破坏。南方周末记者 林方舟/摄
赶海旅游的火热,与众多赶海博主通过短视频、直播放大了赶海的趣味性和戏剧性有很大关系。5年前的2020年9月,抖音的“赶海”线月,该线多次。
“如果屏幕前的家人们喜欢赶海,可以了解一下我们家的1号链接。”9月,“桦加沙”台风来临前夕的夜晚,面朝黑漆漆的大海、两台手机和一盏补光灯,北海艺术设计学院的大三学生姚姚坐在海滩旁,熟练地重复着话术。
姚姚是一家赶海商户聘请的兼职主播。每小时工资30元,每销售3000元能获得100元提成。旺季,姚姚每天直播六七个小时,生意好时一天能卖一万多元的门票,月收入可以过万。这是姚姚兼职的第二个赶海商家。2024年,在第一家商户兼职时,老板还花了4000 元,送她和男友去专门学习直播话术。
在北海赶海商户看来,以直播、短视频的兴起为分界,线上平台可大致分为两代。传统平台是美团、大众点评、携程、飞猪、马蜂窝等;新一代平台则是抖音、小红书和微信视频号等。2024年,抖音上关于赶海的短视频不需要主动推广,随着竞争加剧,2025年开始,商家需要“投流”,即为直播和短视频购买流量和曝光度。
赶海商户“渔家赶海”的老板阿多的经验是,要想获客,必须做到头部水平,连腰部都不行,而且一旦停止投流,排名立马就会跌落。靠着抖音,阿多从行业中游杀入了前三。不过在9月淡季,因为客人太少,他还是停止了抖音直播,可能播一天连主播人工费都赚不回来。
张智英算了一笔账:如果要获得与目前顶级规模商户同等的曝光度,投流费月均支出3万-4万元。2025年,北海赶海生意的头把交椅,属于一家新成立的商户,赶海商户都在传,这家商户老板砸下了几十万元投流。
下村附近海域退潮时,海水能退到离岸边五公里以外。在此长期生活的人,都能观察到一个明显的迹象:赶海的地点离岸边越来越远了。
由于赶海地距离岸边至少有两三公里,不少游客都会乘坐摩托车,单程收费30元。本地人谢强靠摩托车拉客,高峰期每天收入可达近千元。他观察到,旅游旺季,滩涂上每天至少有两百至三百名“的哥”拉客。
这些摩托车都做了改装:座椅焊上钢架、垫上泡沫,加长的座椅还可以坐下“两大一小”;后轮两侧装上了更长的脚蹬,方便游客坐得更稳;轮胎周围加上“升级版”挡泥板,挡住飞溅的海水;侧面挂着一把铁锹或锄头。
由于长期被海水腐蚀,在滩涂上穿行的摩托车的火花塞、化油器、轴承、链条等需要频繁保养和更换。村子附近的摩托车行和修车铺,也成了赶海“产业链”的受益者。
为了节省车费,游客经常选择“拼车”——一辆车坐三个成年人。南方周末记者乘坐的一辆经两轮摩托车改装而成的三轮车,甚至坐了5人,这在几年前已被当地禁止。驶过坑坑洼洼的滩涂,摩托车几乎能把游客甩下来。
经两轮摩托车改装而成的三轮车,已被当地禁止,却仍有“漏网之鱼”正在载客。南方周末记者 林方舟/摄
而经摩托车反复轧过的滩涂,沙质变得硬邦邦的。王俊杰告诉南方周末记者,硬化滩涂破坏了鲎的栖息环境——退潮后,鲎喜欢生活在沙质松软、有表层浮水的滩涂,硬化沙质无法含水,不适宜依靠腮呼吸的鲎栖息。
王俊杰等人于2025年4月发表的论文指出,游客赶海地与幼鲎集中分布区重叠,为鲎种群的栖息引入了生存隐患,包括:影响鲎分布和觅食,人车穿行增加鲎种群“路杀”风险,采挖行为带来误捕、误伤隐患等。鲎在地球上生存了超过4亿年,挺过了五次生物大灭绝,直到近几十年,各地种群数量才因栖息地丧失、过度捕捞等断崖式下降。
不同于一般的封闭式景区,目前沿海滩涂的法律属性处于模糊地带。河北环境工程学院学报发布的论文《我国沿海滩涂法律属性研究》提到,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》等法律,沿海滩涂的法律属性可以被视作土地、海域或者湿地。这也导致滩涂的管理权属在真实的情况中经常发生争议,削弱了管理效果。
对于游客而言,赶海是难得的亲近自然的机会,但不科学的赶海行为可能会破坏自然生态。
据央视等新闻媒体报道,在珠海的网红赶海地唐家湾,游客赶海对贝克喜盐草海草床导致非常严重破坏。其是一种古老的海草,具有固沙、净化水质等重要的生态功能,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(IUCN)列为濒危物种。
吴老二回忆说,十年前,北海赶海旅游刚萌芽时,离岸边几百米就有许多收获,现在,旺季时游客不得不到离岸两三公里外,才能挖到海货。如果步行,至少要半小时以上。
在北海下村滩涂,当地渔民靠海吃海,通常遵循着“抓大放小”的可持续赶海传统,不抓体长小于8厘米的蛏子和体长小于5厘米的车螺。但赶海游客并不会考虑这些,不加分辨地采集一切海洋生物,它们离开生境后很快死亡。
美境自然在北海发起 “空桶行动”,鼓励游客在体验赶海之余,携带空桶上岸,放归不可食用或体型过小的生物。美境自然项目经理董亦非告诉南方周末记者,大部分人了解到“空桶行动”的理念后都愿意配合。但向导吴老二的同事说,曾有游客抓到过保护动物鲎,并没有听从工作人员的劝说,执意要将其带离。
王俊杰说,从当地居民的观察中能证明,赶海行为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显而易见。然而,目前并没有严谨的科学研究,论证一片滩涂的生态承载量到底是多少,抑或赶海行为究竟产生了哪些生态影响。
赶海生意的内卷式竞争,导致商家利润减少,也促使商家开辟新的获利渠道,一种不合法的灰色生意——围网赶海,近年来也开始在北海流行。
所谓围网赶海,也被一些商家美化为“深度赶海”,是渔民在离岸数公里的地方设置漏斗形的围网(渔箔),退潮时拦住海洋生物,让游客进入围网中体验捕捞。围网赶海要去往比普通赶海离岸更远的地方,对潮水的水位深度有要求,每个月只有不到十天可以开放体验。除了作为旅游项目,也是传统捕鱼方式之一。
然而,这种围网的网眼细小,体型很小的海洋生物也难以逃出,也被称为“绝户网”,因不符合可持续捕捞原则,早在2013年就已经被原农业部明令禁止。
体验围网赶海存在不小的安全风险隐患。9月底,台风“桦加沙”刚离开北海没多久,海风大到必须要大声喊话才听得清楚,游客先自行穿过一段齐腰深的涉水路段,努力平衡不在海水中摔倒,然后坐上向导的改装摩托车,去往离岸3公里之外的围网,水位达到大腿处。“没事的,放心吧,我们比你们更怕出事。”向导宽慰。
抵达渔箔后,游客们拿起抄网,奋力打捞被困住的鱼虾蟹。在商家发布的短视频里,围网中都是大螃蟹、金鲳鱼、皮皮虾等“硬货”,但实际捞上来的,几乎只有小鱼小虾。见用抄网打捞的效率太低,几位向导随后又拉起渔网,游客们争相挑拣相对值钱的海货。待游客挑完后,渔民再收网,将剩下的沙丁鱼等运到岸上售卖。
一位向导全程在举着手机直播,以吸引更加多的潜在客户。“前几天下村清理围网,你听说了吗?”南方周末记者问道。“我在直播,这个不能说。”向导迅速终止了话题。走出围网,视野范围内还竖立着其他大大小小的渔箔。
2025年9月22日,北海的围网赶海生意被央视焦点访谈点名。下村滩涂属于广西北海滨海国家湿地公园的管辖范围,9月23日、24日,湿地公园管理处对辖区内的渔箔、地笼、地网等非法渔具进行了排查和清理。
9月26日,南方周末记者在距离下村10公里的西村,发现仍旧能付费体验围网赶海,这里拥有和下村一样的滩涂、一样的生物、一样的天气,只是不属于湿地公园的管辖范围。电子商务平台显示,体验价188元/人起。
围网赶海生意利润可观。经营围网赶海的商户曾多次找张智英合作,每介绍一位客人,给他50元“人头费”,但都被他拒绝。“按照我们的客流量,如果做这个的线月,湿地公园管理处拒绝了南方周末记者的采访请求。一位工作人员称,虽然这些非法渔具已影响到海洋生态环境,但湿地公园管理处对非法渔具没有执法权,无权直接拆除,只能联合海洋执法部门管理,给日常管理增加了不小难度。
(吴老二、“沙虫哥”、姚姚、阿多、谢强为化名,南方周末实习生唐珠安冬对本文亦有贡献)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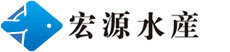
 0591- 62760999
0591- 62760999


